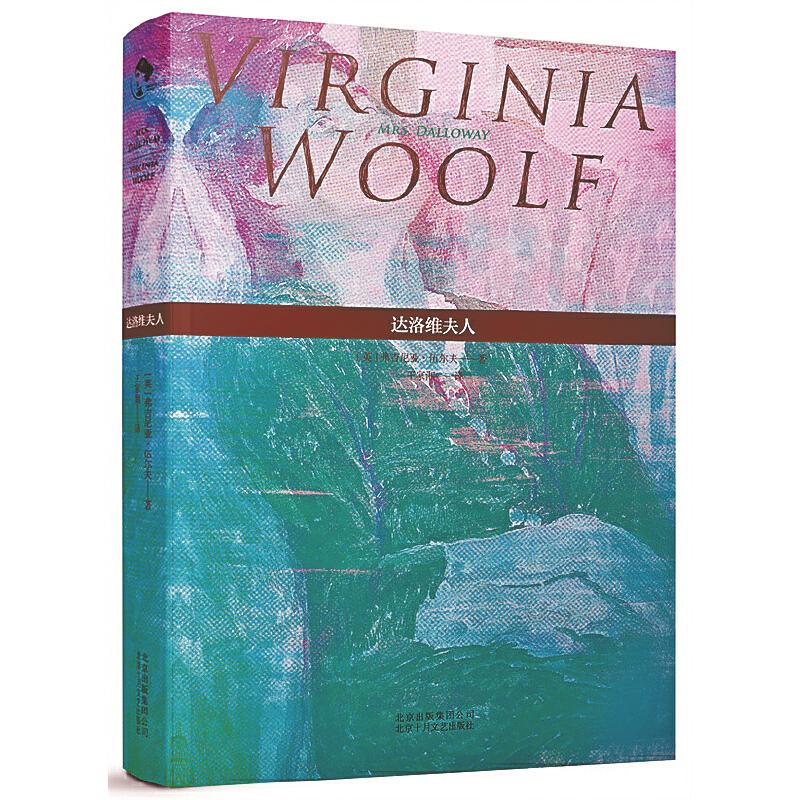□刘 丽
世界是一个荒岛,人潮宛如拍打着它的海浪。在风或日月引力的作用下,两个完全陌生的人竟然在某一个时间点实现了在荒岛上的位置共享。在哲学意义上这可能就是存在的偶然、荒诞和神奇吧。
和小欧的相识便带着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甚或是夸张的剧本感。那是2019年,我在“三联中读”App里买了一个哲学课程,然后被拉入一个几百人的大群。某一天,兴之所至,我在群里问了一句:有人喜欢阿兰·德波顿么?
不过是一个不见得有多少意义的问号,不过是一条微小到几乎不见波澜的信息,想不到有人立刻回应了我,她就是小欧。其时,我正在读阿兰的《拥抱逝水年华》,正是这一本书,开启了我对普鲁斯特的兴趣。也正是源于对普鲁斯特的热爱,之后我俩都进入了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的读书群。虽然性格均属内向的我俩在群里彼此之间的直接交流并不多,但我还是积累了对小欧的一些了解:她的文学启蒙是卡夫卡,因为博尔赫斯的书认识了爱人小别,在美国陪读了几年后又一起回国,两个人在苏州安了家,去年生下了女儿小摩拉。
我其实是个边界感特别强的人。虽然看着性格温和、容易相处,但真正能接近我且生出亲近感的人几乎没有。我一直觉得人世是属于个人的荒原,保罗·策兰曾写过:“荒凉,织进了我们四周的白昼。”假如在人世间能幸运地遇见一两个可以深谈者,便恰似在荒野看见洁白的野百合,于一阵沁人心脾的芬芳之中含笑相认,喜悦不已。亦如诗经所云:“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相识7年之后,在2025年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和小欧相约见面了,只可惜那时的风并无一丝凉意,仍然夹带着烘烤似的恼人气息。
见面的这一天清晨,我有点坐立不安。很早就醒了,然后起身在楼顶浇了我的花,又将书桌上的花瓶换了水。花瓶里插着一枝镰仓长夏,紫蓝色,圆如满月,大如头颅。插在花瓶里的它仿佛是一朵巨大的云彩,有着印度洋一样迷人又诱惑的渐变色。花瓶放在书桌上,每次我坐下来的时候都会顺手给它洒点水,如此炎热天气之下这枝绣球竟保持了10天。我想要它的鲜活更持久一些,但心中明白世人所渴望的持久或永久不过都是一些虚幻之光,都是一夕朝露罢了。恐怕在“永久”这个词背后永久的只能是变形或消失。
当天上午11点多,我终于在酒店见到了小欧一家:小欧、小别、小摩拉还有小欧的妹妹。
小欧穿着一件温暖的杏粉色碎花连衣裙,衣服上的印花有又细又淡的树叶和深红的小圆果子,我辨认不出那是樱桃果还是山楂果,不过我情愿它们是山楂果。因为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过山楂树,也给了它们一种象征意义:以天然的姿态融入回忆的巨厦,成为对抗时间流逝的永恒印记。
因为我说了一句“与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小欧便追问我哪里不一样。或许是看惯了她的那个圆脸大眼睛的漫画头像,不自觉地就会把一些漫画特质投射在想象中吧,比如言笑晏晏或甜美天真,但我一时又表达不出,只好挠挠头说:“以为你是长头发。”毕竟我一直觉得小欧是一个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女生。
现在仔细回想我们彼此之间的聊天,似乎引起小欧兴趣的都是关于写作的一些问题,比如究竟是什么导致我开始写字,或具体是什么时间开始写字,或最初受哪个作家影响最大,或写完一篇文字之后会不会觉得身心疲惫。
小别是中科院的博士,之后去美国读了博士后,专业是生物制药。我们还聊了一些医疗医药的话题,我感觉小别有点像卡夫卡《城堡》里面的土地测量员,身上有着人类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有的挣扎或在荒诞世界中寻求归属和意义的努力。
我问:“觉得生活有压力吗?”小别表示她不会忧虑未来,又自称对所有人的生活姿态都能够理解。这不免让我惊讶,不忧虑未来想必是更注重事物的过程而忽略其结果,而能深度理解他人的人想必也已经深度认识了自我。
小欧一直居家照顾小摩拉,脸上有一些疲惫的痕迹,说是晚上睡不好,还脱发。我问她的理想,她告诉我,希望在陪小摩拉一起长大的同时也能治愈自我的阴影。她问我现在看什么书,我说:“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小欧是“90后”,山东人,我们之间有着20岁的年龄差距。她问我:“现在的你和10年前的你有什么区别?”
我想了想,在逝去的那些岁月里,当我用尽全力从偏执的深渊里跳出,这一刻的我看待万事万物的目光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我说:“可能不再有执着之心了吧,看待事物更随意和顺其自然。”
据说宿命般的相遇都是创伤性的,也会特别令人成长。如今的我更习惯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在人间穿行,观察自然,观察他人,也观察自己。
很少有人知道像我这样一个在人间总是显得被动,很少起意去探寻他人的人,在自我的世界里竟是无比积极主动的。无论如何,像我这样一个在意识的河流中漫无目的地写字的人总是可以在文字之中看到春风吹起、秋雨袭来,看到花开如雪、雷电轰鸣,它们带来的感受已经足够丰富。在人世之中被爱或被懂得固然好,但如若没有,也不过就是像济慈所说的那样:“我可以近乎孤独地度过一生”。
这也没什么不好。生命原是一种步伐和节律,而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或记录,体验悲欢离合,记录形神从丰美至凋亡,而作为一个人间生命体存在的终极意义,或许是努力顺应真实的自我并接受人生的无意义吧。